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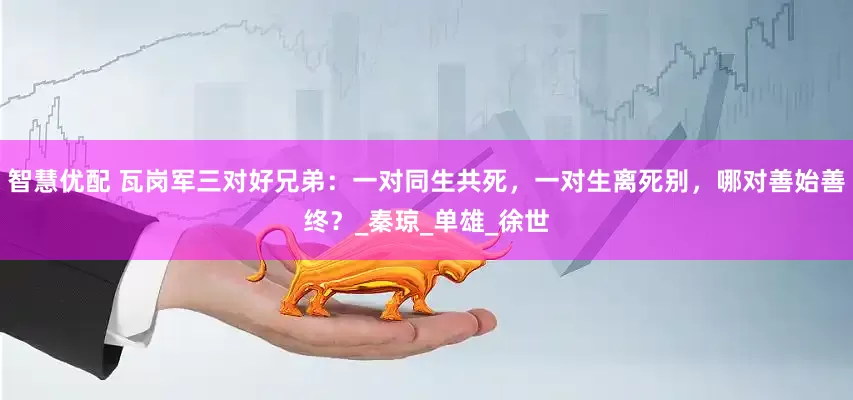
宁学桃园三结义,不学瓦岗一炉香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人虽然没有正式举行过结拜仪式,但他们之间的情谊比很多亲兄弟还要深厚。至于瓦岗群雄是否曾有过烧香磕头之事,读过《隋唐演义》的人应该都知道其中的差异。演义小说中,瓦岗的英雄们通常由“贾家楼四十六友”组成,但仔细研究历史,我们不难发现,这些“兄弟”不仅身份地位天差地别,甚至年龄差距也极大,根本不可能坐在同一桌上共饮一杯,更谈不上结拜为兄弟了。
尽管小说中所描绘的四十六位瓦岗英雄是虚构的,但在这些英雄中,确实有几位情深意重、舍生忘死,甚至留下了可供查证的史实。翻开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,我们会发现,瓦岗群英中有六位人物结为生死兄弟,他们的结局迥然不同,令人唏嘘:有的同伴长眠,共享死后安宁;有的生死离别,结局充满悲凉;而其中秦琼的兄弟情,更是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微妙的变化。
在正史中,单雄信与秦琼之间不仅没有结义,反而有着深厚的仇怨。秦琼的上司张须陀,曾是齐郡通守、河南道讨捕大使,他的死与单雄信、翟让、李密以及徐世勣等人密切相关。张须陀在战斗中为救被困的部下英勇牺牲,虽然他成功突破了瓦岗军的包围,但最终因不舍同袍而丧命。《隋书》记载了张须陀的壮烈:“密与让合军围之,须陀溃围辄出,左右不能尽出,须陀跃马入救之。来往数四,众皆败散,乃仰天曰:‘兵败如此,何面见天子乎?’乃下马战死。时年五十二。其所部兵,尽夜号哭,数日不止。”
展开剩余72%秦琼加入瓦岗军并非出于心愿,而是迫于无奈。《旧唐书》记载,秦琼原本跟随张须陀作战,但随着张须陀的死,他转投裴仁基。令人感到诧异的是,他与自己曾是生死兄弟的罗士信逐渐疏远,而与裴仁基的关系变得亲密。罗士信和秦琼曾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兄弟,但随着裴仁基的接纳,罗士信不再和秦琼保持密切的联系,反而与裴仁基更为亲近。甚至,罗士信的忠诚开始转向裴仁基:“士信初为裴仁基所礼,尝感其知己之恩,及东都平,遂以家财收敛,葬于北邙。又云:‘我死后,当葬此墓侧。’及卒,果就仁基左而托葬焉。”
罗士信与裴仁基并不是兄弟,但当秦琼投降唐朝时,罗士信却另寻途径投降李渊,并迅速被封为陕州道行军总管,成为唐朝方面军的司令,彻底与秦琼分道扬镳。罗士信和裴仁基的埋葬地也同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,但在这些瓦岗英雄中,王伯当和李密的情谊才是最为深厚的。
王伯当在瓦岗军时,一直是李密的心腹兄弟。在李密设法除掉翟让之后,王伯当更是充当了调解者,保护了单雄信和徐世勣的性命。王伯当对李密的忠诚无条件甚至无原则,这种情谊在他们归唐后依然未变。李密被封为光禄卿,王伯当被封为左武卫将军,而秦琼则是后来才通过玄武门之变获封左武卫大将军。
然而王伯当并没有选择安享高官厚禄,他坚持要与李密一同前行,最终同赴黄泉。在唐朝历史上,王伯当的忠诚被铭记,而他与李密的并肩死去,使得他们的情谊更加刻骨铭心。在《旧唐书》里记载:“义士之立志也,不以存亡易心。伯当荷公恩礼,期以性命相报。公必不听,今祗可同去,死生以之,然终恐无益也。”尽管结局充满悲剧,但王伯当的忠诚让他成为了真正的义士。
而单雄信与徐世勣的故事则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与悲凉。单雄信原本是瓦岗军的骨干,但在翟让被杀之后,他选择了投靠王世充,而徐世勣则带领瓦岗的部队归唐。尽管两人的道路完全不同,但他们的情谊并未因此而改变。单雄信曾有机会在东都洛阳的战斗中击败李世民,但在徐世勣的劝阻下,他选择放过李世民,最终因而错失了战功:“太宗围逼东都,雄信出军拒战,援枪而至,几及太宗,徐世勣呵止之,曰:‘此秦王也。’雄信惶惧,遂退,太宗由是获免。”
然而,尽管单雄信曾为了徐世勣放弃了击败李世民的机会,最终他还是未能逃脱命运的安排。李世民并没有因为徐世勣的情谊而放过单雄信,最终,单雄信还是死于李世民之手。
相比之下,秦琼与程咬金的结局显得要“善终”得多。两人起初并不富裕,都是凭借一腔热血投身战场,反抗暴政。程咬金虽然曾是盗贼,但他并没有从事过伤天害理的行为,而是与秦琼结伴并肩,最终投降李唐,并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。最终,他们分别受封为翼国公和宿国公,享受了荣耀的晚年。程咬金甚至在玄武门之变前,劝李世民“速自全”,并因此得到更高的评价。
因此,这三对“生死兄弟”最终的结局都充满了曲折与感慨。王伯当与李密的结局深刻体现了忠诚与牺牲,单雄信与徐世勣的故事则是兄弟情深但终究难以挽回的悲剧,而秦琼与程咬金,则是为数不多的“善始善终”的英雄。你怎么看呢?这三组兄弟中,哪一组最讲义气?王伯当、单雄信、秦叔宝,谁才是瓦岗群英中的第一义气英雄?
发布于:天津市创通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